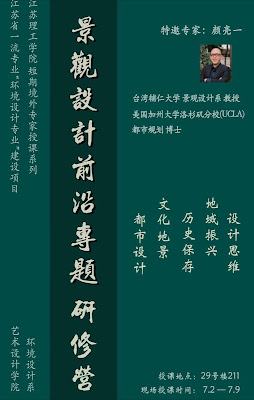「無政府」在日常用語中往往用來形容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不過這剛好說明了一般人對這個字眼的誤解。如果我們分析「無政府」英文anarchy的構成,會看到其字根-archy事實上意謂了「統治、支配」,而字首a-乃是「不、無」的意思,所以anarchy的原始意義是「無統治」或者「不受支配」的意思。「無政府」被用來形容混亂失序,是因為一般人認為一個沒有統治者的社會必然會帶來完全沒有秩序的狀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反之,真實的(理想)無政府狀態是自由的人民自發性地通過互助的關係共同建立了社會秩序,一種不是由更高的權力者強加的秩序。人類學家已經證明,原初社會的游獵部落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無政府的社會關係上,甚至這些部落還藉由部落之間恆常的禮物交換或戰爭,以避免更高層級統治機構的形成(柄谷行人 2013)。即使在定居社會形成以後,依無政府原則建立的自治社區仍然廣泛側身於古代的中國、古印度、古希臘、羅馬時代、中世紀的歐洲、乃至於近現代的國族國家之中。
柄谷行人(2014)通過對鄂蘭與亞里斯多德著作的閱讀,解釋了無政府主義的運作原則,也就是希臘文中的isonomia,意即無支配。柄谷指出,古希臘城邦由於貨幣經濟帶來階級對立,許多市民淪為債務奴隸。為解決這個問題,民主制(democracy,人民支配)被發明出來,其手段主要有兩個形式。第一種以斯巴達的民主制為代表,國家廢止交易,實施經濟平等,但犧牲了人民的自由。第二種則是以雅典的民主制為代表,該城保持市場經濟自由,言論自由,但是經由國家,向少數富人徵收財富,進行重分配,以帶來平等。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民主制,自由與平等之間都是相互矛盾的,必須通過國家來對社會進行干預。此外,為了保持民主制的運作,這兩個城邦都需要征服其他城邦以獲得奴隸,市民(只有男性可以成為市民)的公共生活主要就是參與政治以及戰爭,把維生所需的勞動交給奴隸(以及女性)。結果,這兩個城邦都建立了軍事化的國家,並形成排外的國族主義。
相對地,當時在愛奧尼亞(今土耳其西部)的城邦卻發展出了不同的政治型態。愛奧尼亞的城邦是由希臘移民所建立的,他們脫離了原先氏族社會,在新的土地上發展獨立自營的農業與工商業,並且擁有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同於希臘城邦,愛奧尼亞城邦相當重視勞動與交換的價值,而且城邦是以工商業者的評議會為中心,交易活動是私人的事業,而非國家的事,在這裡產生了沒有支配性的isonomia制度。由於這個制度不經過民主化或階級鬥爭出現,而是透過移居產生,因此自由和平等並不互相衝突,自由反而帶了平等。萬一發生了經濟不平等的狀況,沒有資源的居民就會移民到別的地方,產生了類似游獵社會的流動性。不過,isonomia 的實踐通常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有充份土地,二是沒有鄰國的威脅,因此這種例子通常發生在新近移民的社會,如西元10到13世紀的冰島,當時的人口是由厭惡維京人社會的挪威移民所形成,他們沒有中央政府也沒有軍隊,一切事務都由農民的集會決定。另一個例子是18世紀北美東部由英國移民所建立的自治城鎮(township),這些市鎮是由評議會(town meeting)運作,在維持其自治性的同時,也與其他市鎮形成邦聯,形成郡縣(county),而各自治的郡縣再以邦聯的方式形成州(state)。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東南亞內陸被稱為贊米亞(Zomia)的廣大山區,這個裡住的是自17世紀以來來逃避周邊平地國家的流亡者,並且在此形成了無數游耕部落,他們的文化、語言、經濟、生活方式都為了抵抗國家支配而發展出來(Scott 2018),因此也是一種isonomia的實踐。在這裡我們看到,空間中的移動與逃逸乃是一個isonomia的關鍵因素。
現代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主張與學說,則是從18紀世開始的,代表性理論家家包括高德曼(William Godwin)、普魯東、巴枯寧、克魯特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者強調自由,反對包括國家在內的各種壓迫性權威;他們認為國家是人為製造的,而社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只要取消除國家的強權支配,人的天性即可在社會中經由教育與學習開展出來。在一個有秩序而無國家支配的社會中,擁有自由意志的個人將通過自願聯合與自願組織來處理公共事務,並能使物質利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王遠義 2004, 400-402)。促成其發展的歷史因素則包括法國大革命、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及科學主義:在法國大革命中他們看到中央集權國家對人民的壓迫;而工業資本主義則造成了財富集中與生產制度的集體化,國家正是這個系統的執行者;最後,他們相信運用科學方法理解社會與建設新社會,可以創造無支配與壓迫存在的社會秩序(王遠義 2004, 404-405)。簡而言之,無政府主義者的目標是企圖在現代社會中建主以一個類似isonomia的政治型態,讓自由與平等得以共存,同時實現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而達成這個目標的首要工作就是廢除國家。
至於無政府主義和地理的關係,在早期理論家的作品中就已經顯現出來(Spring 2016, 28-30)。高德溫(Goldwin [1793]1976)就明確反對政府及其有關財產、君主政治、法律等制度,因為它們會阻礙自然進步的人性。高德溫對於國家的批判已經隱然為無政府主義帶進了地理的向度,而普魯東(Proudhon [1840]2008)則更進一步探討工業革命如何影響了人類在空間中安排與制度化其相互關係的方式,並提出其最知名的主張「財產即盜竊!」,財產制度就是批准某些人從人類共同享用的公地上把財產偷走,在此,他建立了財產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性地理學概念。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則聚焦於人們如何在利他主義與共同互動的背景下建立一個自由社會,他認為國家領域性的機構必然是暴力且反社會的,同時否定了可以促進實現人性的另翼非階層性社會與空間組織形式(Bakunin [1873]2002)。由上述三人的主張當中,我們看到在早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中,已經暗示了一個地理學的架構。
緊接這些無政府主義先驅者的兩位思想家,雷克呂斯與克魯特泡特金,本身就是地理學家,同時也為無政府主義奠定了科學的理論。雷克呂斯(Elisee Reclus 1894)設想了一種人性和地球本身的聯合體,並認為人性乃是「自然成為自覺」。他認為地理學必須整合「解放性的社會轉型」,並將視野大幅擴展,以包含階級、種族、性別、權力、社會支配與組織之形式與規模、都市化、科技、以及生態等議題。此外,他還致力在家庭、國家、甚至物種之外拓展同情、利他、以及愛的能力,因為他認為這個過程可以同時否定並減少任何形式的支配(Spring 2016, 31)。而克魯特泡特金(Kropotkin [1902]2008)則根據他在西伯利亞對動物以及前封建社會的觀察得出一個結論,一反當時流行的強調「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義,互助以及自願性合作才是物種生存與演化最重要的能力。他的地理學想像因此和馬克斯主義者非常不同,他強烈質疑由產業工人所組成中央政府的想法,而主張由農業、在地生產、去中心化組織所構成的自足社會型態(Galois 1976)。
普魯東、雷克呂斯、克魯特泡特金等人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沃德(Colin Ward)與布克欽兩位二戰以後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沃德主要的研究焦點在於住宅與都市規劃,他認為現代都市規劃被官僚與開發商所控制,雖然打著服務窮人的名號,但實際上是消滅窮人的社區。之所以會產生這個問題,是因為官僚系統無法容忍混亂與失序,而追求和諧一致的社會與空間秩序以及淨化的社區。然而,這種追求社會一致性的欲望其實是對社會發展有害的,因為根據愛律克森(Eric Erikson)的發展心理學,只有青少年才會想找到淨化的身分認同,真正的成人不但能接受多元和混亂,而且能從中發展自我,因此中央集權的城市規劃等於是協助一個社會把人凝結在青少年時期,斷絕人們長大成人,也造成了內向排外的社區與城市。因此,社會與空間的規劃的權力必須放在市民手上,讓他們在混亂的狀態中自己克服社區內不同利益與文化的衝突,而非由國家權力自外部加以干涉。而由個別社區之間經過協商所形成的邦聯,將可以形成一個無政府城市(anarchy city,Ward 1973)。就地理學向度而言,布克欽也主張社會與空間組織的權力應該座落在最基層的在地社區。在他所謂的「自由意志城鎮自治主義」(libertarian municipalism)中,布克欽認為基進的政治應該始自創建像是社區大會、市鎮評議會、社區議會等在地民主結構,在這些公共領域中,「成熟的個人應可以直接處理社會事務,就像他們處理私人事務一樣」,而在其中經濟自治是乃是最重要的議題,而這可以讓社會走向不同的道路,擺脫「集中化的國族國家以及建立在利潤、競爭、與盲目成長的經濟」(Bookchin 1995, 224)。
綜上所言,無政府主義與社區的關係可以歸結如下:首先,人類與人類、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應該建立在互助與合作而非競爭與支配上;其次,人類經濟與政治事務的治理基本單位應該在分散的自治社區,由所有市民直接參與決策;第三、為了處理更大空間尺度上的經濟與政治議題,各自治社區可以自主形成自治的聯合體,而非通過霍布斯式的社會契約把權力交給中央集權的國家;最後,唯有通過建立這種無支配性的政治制度,才能同時達成自由與平等的目標,並該人性得到最好的發揮。